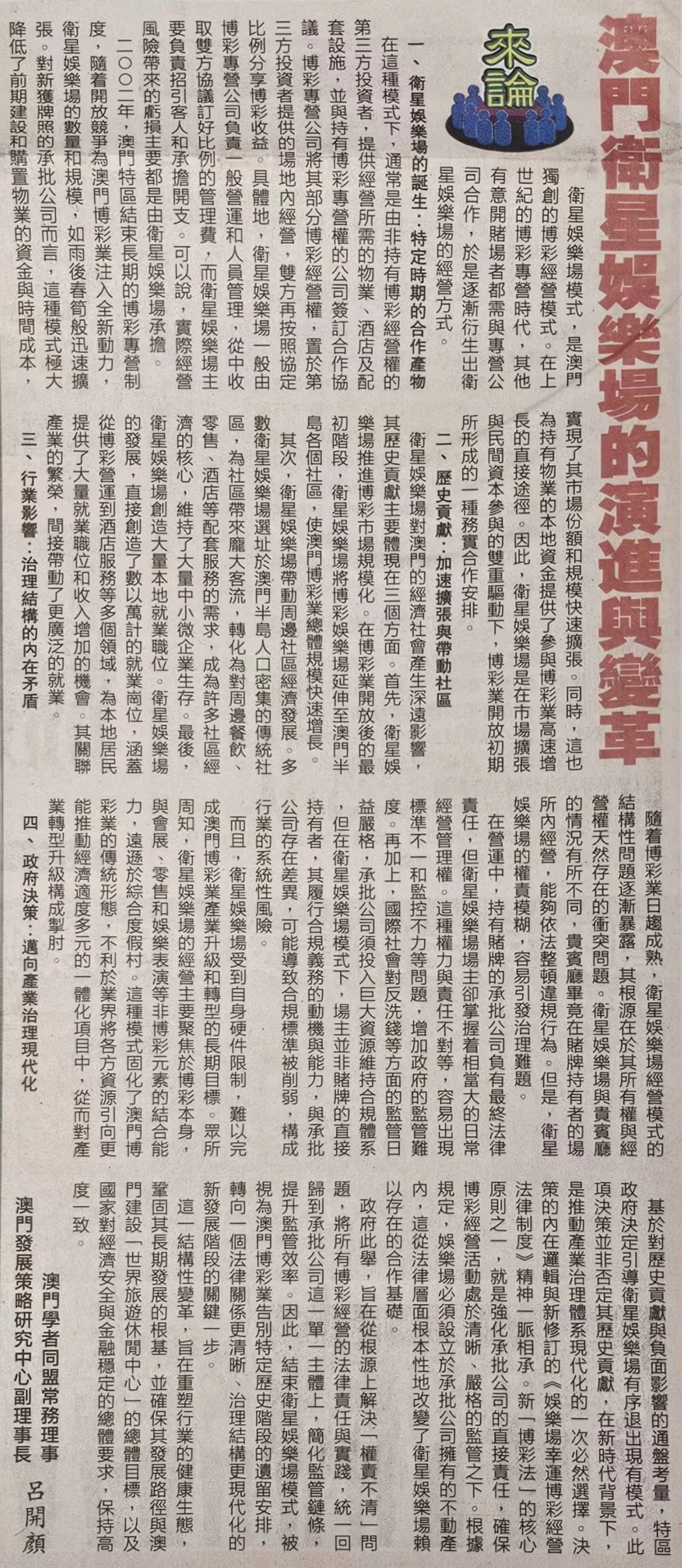衛星娛樂場模式,是澳門獨創的博彩經營模式。在上世紀的博彩專營時代,其他有意開賭場者都需與專營公司合作,於是逐漸衍生出衛星娛樂場的經營方式。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呂開顏表示: 一、 衛星娛樂場的誕生:特定時期的合作產物
衛星娛樂場模式,是澳門獨創的博彩經營模式。在上世紀的博彩專營時代,其他有意開賭場者都需與專營公司合作,於是逐漸衍生出衛星娛樂場的經營方式。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呂開顏表示: 一、 衛星娛樂場的誕生:特定時期的合作產物
在這種模式下,通常是由非持有博彩經營權的第三方投資者,提供經營所需的物業、酒店及配套設施,並與持有博彩專營權的公司簽訂合作協議。博彩專營公司將其部分博彩經營權,置於第三方投資者提供的場地內經營,雙方再按照協定比例分享博彩收益。具體地,衛星娛樂場一般由博彩專營公司負責一般營運和人員管理,從中收取雙方協議訂好比例的管理費,而衛星娛樂場主要負責招引客人和承擔開支。可以說,實際經營風險帶來的虧損主要都是由衛星娛樂場承擔。
二○○二年,澳門特區結束長期的博彩專營制度,隨着開放競爭為澳門博彩業注入全新動力,衛星娛樂場的數量和規模,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擴張。對新獲牌照的承批公司而言,這種模式極大降低了前期建設和購置物業的資金與時間成本,實現了其市場份額和規模快速擴張。同時,這也為持有物業的本地資金提供了參與博彩業高速增長的直接途徑。因此,衛星娛樂場是在市場擴張與民間資本參與的雙重驅動下,博彩業開放初期所形成的一種務實合作安排。
二、 歷史貢獻:加速擴張與帶動社區
衛星娛樂場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產生深遠影響,其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。首先,衛星娛樂場推進博彩市場規模化。在博彩業開放後的最初階段,衛星娛樂場將博彩娛樂場延伸至澳門半島各個社區,使澳門博彩業總體規模快速增長。
其次,衛星娛樂場帶動周邊社區經濟發展。多數衛星娛樂場選址於澳門半島人口密集的傳統社區,為社區帶來龐大客流,轉化為對周邊餐飲、零售、酒店等配套服務的需求,成為許多社區經濟的核心,維持了大量中小微企業生存。最後,衛星娛樂場創造大量本地就業職位。衛星娛樂場的發展,直接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,涵蓋從博彩營運到酒店服務等多個領域,為本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就業職位和收入增加的機會。其關聯產業的繁榮,間接帶動了更廣泛的就業。
三、 行業影響:治理結構的內在矛盾
隨着博彩業日趨成熟,衛星娛樂場經營模式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,其根源在於其所有權與經營權天然存在的衝突問題。衛星娛樂場與貴賓廳的情況有所不同,貴賓廳畢竟在賭牌持有者的場所內經營,能夠依法整頓違規行為。但是,衛星娛樂場的權責模糊,容易引發治理難題。
在營運中,持有賭牌的承批公司負有最終法律責任,但衛星娛樂場場主卻掌握着相當大的日常經營管理權。這種權力與責任不對等,容易出現標準不一和監控不力等問題,增加政府的監管難度。再加上,國際社會對反洗錢等方面的監管日益嚴格,承批公司須投入巨大資源維持合規體系,但在衛星娛樂場模式下,場主並非賭牌的直接持有者,其履行合規義務的動機與能力,與承批公司存在差異,可能導致合規標準被削弱,構成行業的系統性風險。
而且,衛星娛樂場受到自身硬件限制,難以完成澳門博彩業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長期目標。眾所周知,衛星娛樂場的經營主要聚焦於博彩本身,與會展、零售和娛樂表演等非博彩元素的結合能力,遠遜於綜合度假村。這種模式固化了澳門博彩業的傳統形態,不利於業界將各方資源引向更能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一體化項目中,從而對產業轉型升級構成掣肘。
四、 政府決策:邁向產業治理現代化
基於對歷史貢獻與負面影響的通盤考量,特區政府決定引導衛星娛樂場有序退出現有模式。此項決策並非否定其歷史貢獻,在新時代背景下,是推動產業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次必然選擇。決策的內在邏輯與新修訂的《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》精神一脈相承。新“博彩法”的核心原則之一,就是強化承批公司的直接責任,確保博彩經營活動處於清晰、嚴格的監管之下。根據規定,娛樂場必須設立於承批公司擁有的不動產內,這從法律層面根本性地改變了衛星娛樂場賴以存在的合作基礎。
政府此舉,旨在從根源上解決“權責不清”問題,將所有博彩經營的法律責任與實踐,統一回歸到承批公司這一單一主體上,簡化監管鏈條,提升監管效率。因此,結束衛星娛樂場模式,被視為澳門博彩業告別特定歷史階段的遺留安排,轉向一個法律關係更清晰、治理結構更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的關鍵一步。
這一結構性變革,旨在重塑行業的健康生態,鞏固其長期發展的根基,並確保其發展路徑與澳門建設“世界旅遊休閒中心”的總體目標,以及國家對經濟安全與金融穩定的總體要求,保持高度一致。
呂開顏 (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、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)